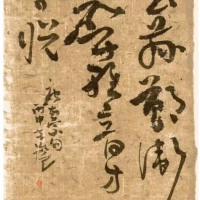假如你有幸穿越回了唐代,那么每到天气转寒,秋风乍起的时候,就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妇女们纷纷挽起衣袖,手执木杵,身披月光,两两相对地在捣衣……
你也许要问:这捣衣究竟是什么活计啊?
你在南方可能会看见妇女在河边洗衣,将衣服放在石头上,用木棒捶打,这可不是捣衣。原来,“捣衣”又称“捣练”,是古代制作衣服的一道重要工序。
“练”是一种生的丝织品,刚织成的时候质地坚硬,必须经过煮沸、漂白,再把它放在砧石上,用杵棒捶击,才能变得柔软,方便缝制。
这么说可能太抽象了,咱们不妨来看看唐代宫廷画家张萱绘制的《捣练图》就一目了然了。这件生动细致、韵味无穷仕女画,画中的人物细节、位置经营均暗藏着一些有趣的安排,细细品鉴,个中奥妙更值得玩味。
唐代名画《捣练图》里的秘密
天水画院摹写的张萱仕女
现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捣练图》(绢本,设色),传为宋徽宗领导下的天水画院摹中唐张萱所作。据宋《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三引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张萱,京兆人(今陕西西安),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仕女等,名冠于时……其画仕女,周昉之(难)伦也。”公元1120 年编成的《宣和画谱》载有四十七卷张萱的作品,其中三十多卷都是描绘仕女的。《捣练图》正是这样一幅描绘唐代宫廷女性捣练劳作场景的手卷式工笔画。

《捣练图》绢本,设色,37cm×145.3cm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此卷画原本没有款识,北宋灭亡后进入金朝宫廷,金章宗完颜璟用“瘦金体”题“天水摹张萱捣练图”,上下两边四个角都有金章宗的收藏印,保存完整。后有元末书法家张绅题诗“乃知蟆母之姿,亦有效其颦者”,清初为著名学者高士奇所藏(卷首书“高江邨清吟堂秘藏”所示)。1912 年5 月,时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部长的冈仓天心从北京一位满清贵族手上购得,同年8 月入藏波士顿美术馆。
捣练,亦即捣素、捣衣,古代妇女协力的日常农织劳作,由夏入秋这一特定时节的生产习惯。具体地说,布料上浆捶捣,称“捣练”;成衣上浆捶捣,称“捣衣”。“练”是一种较为精细的丝帛原料,生衣,是指没有经过浆、捣的织物所制之衣;熟衣的衣料则由经过浆、捣等更精细的过程加工的衣料制成,更适合穿着。
图中女子端庄丰腴,发髻高耸,面有花钿,神情从容,身姿优美,着半露胸式衫裙装,短襦长裙,肩搭披帛。线条匀细、畅达遒劲、饱满而有张力,衣纹变化丰富、图案精致,衣裙薄如蝉翼、轻盈飘逸。色彩浑融调和、富丽典雅、交相辉映,且没有一块颜色雷同。画面疏密得当、张弛有度、节奏感强,头饰、披帛、上衣刻画精细,与长裙和白练之“疏”形成对比;全卷以S 形大开大合整体布势,三组人物有站有坐、高低错落,局部构图各有不同,从右至左分别为圆形、三角、十字交叉形,动静结合、精确巧妙、一气呵成。
《捣练图》最令人叹服之处,是细节的构思与刻画。通常把这幅长约一米五的手卷上的十二个人物分为三个场景,第一组4人捣练的场景中,2 位手持木杵微微用力,2 位放下木杵歇息片刻,从右至左第4位红衫蓝裙女子轻轻倚靠着木杵,用手挽起一侧衣袖,生动写实。石槽中白练两端扎紧,为了防止边缘的丝口遭捣击而断裂。

《捣练图》局部
四位捣练仕女姿态、妆容、服饰各异、动静结合,妙趣横生。
第二组2人对坐,一人低坐于地毯上理线,一人高坐于凳子上缝纫,图中虽看不见细线,但从身姿手势足以判断线的走向。

《捣练图》局部
理线仕女的刻画细致入微,以专注的神态、手姿让观者感受到其中若有若无的丝线。
第三组3人扯练1人熨烫,扯练者因向后用力而后倾,熨烫者一手扶练一手持木柄金属勺状“熨斗”,勺中是烧红的木炭,将捣练时因捆扎而产生的褶皱细细熨平。木炭来自第2 组人物与第3 组人物中间的炭火盆,火盆花纹精美,且三层皆有不同,两侧有提手,配有用来加炭的带链绳的火筷子,最下面一层是空的,用来通风助燃。

《捣练图》局部
蹲下煽火的女孩,与第3组下方侧身弯腰的孩童,是劳作场景中最有情趣的设计:一个手拿扇子扇风,同时因盆里的木炭烧得太热而觉不适扭过脸去,且以袖遮面,分外传神;另一个在白练之下淘气地窜来窜去,饶有兴趣地四下张望,以嬉戏玩耍之态打破聚精会神的单调气氛,使画境活泼而具抒情意味。

《捣练图》局部
生火女孩手持的团扇,其画面充满文人画的趣味,与主体鲜明艳丽的色调形成对比。
团扇暗藏的文人逸趣
相比侧身张望的女孩,生炭火的女孩儿更加为人津津乐道。她右手扇火的扇子引出第三组人物,扭向另一侧的面庞则把目光引向第二组,恰好起到了承前接后的“转场”作用。

《捣练图》局部
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这个女孩儿手上那把团扇的扇面。扇面很小,图像并不十分清楚,隐约能够辨认出的是水面、芦苇、雪和岸上水鸟一对。扇面整体感觉却因为色调和构图而分外明确——平静、荒寒、萧索,与《捣练图》这一典型的仕女图在色彩上的热烈、鲜艳、绚丽形成强烈反差,却是文人画常见的画题和趣味。这幅小小的扇面(权且将其命名为“秋临江岸”),是宋徽宗领导下的天水画院的画工们留下的时间通道,在精细而考究地摹画唐代工笔人物画名作时,将宋代趣味的蛛丝马迹有意无意地印在不起眼的角落。
杨孝鸿在其博士论文中梳理了文人画的发展史,他认为文人画的主体包含士大夫和文人逸士两大身份的画家,其所对应的历史从王维数起为文人画之滥觞,宋代的苏轼当为文人画的正式形成期,历经元明两代的转型发展,随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文人画论的出现而臻鼎盛完备。令人疑惑的是,无论从徽宗的作品(或徽宗署名画工代笔的作品)还是他在画院方面的作为来看,赵佶都更像一位院体画家。那么同样是赵佶治下的天水画院如何得以在《捣练图》上留下一方文人画趣味的“秋临江岸”呢?
按图索骥,笔者在张其凤的博士论文《宋徽宗对文人画的影响》中得到的启发极为有益。他认为宋徽宗不仅对院体绘画贡献巨大,而且对文人画的贡献同样不可低估,因为宋徽宗不仅自己有意接受文人画的审美思想,而且也使其亲自关照下的宣和体带有了浓郁的文人画风,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徽宗从画学制度设置的倾向上、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形式感上、文人画绘画思想的探索上,给予文人画以巨大的支持、引领与推动。如此便不难理解《捣练图》上扇面“秋临江岸”作出的小小暗示。

《捣练图》局部
捣练位置蕴涵的巧妙经营
西汉班婕妤有《捣素赋》,“投香杵,扣玟砧”(意为“姑娘们舞起捣衣的木棒,和谐地敲打精美的捣衣石”)。梁朝庾信、唐杜甫、李商隐、宋贺铸等诗人也留下了大量谈及捣练细节的作品。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东晋、南朝画家张墨、陆探微、刘瑱都画过捣练题材。 现在可以看到同样母题的场景,除了传为张萱的《捣练图》,还有长安县兴教寺故址线刻画(初唐),山西盗墓贼偷盗出的画像砖(盛唐),南宋牟益的《捣衣图》和明代佚名《宫蚕图》等。结合这些文字与图像,我们很容易弄清“捣练”这一母题所涉及的步骤:
(1)捣练(类似舂米)
(2)将捣好的素练熨烫平整
(3)裁剪、缝制衣裳
(4)把衣裳装在盒子里寄往远方
这个连贯而合理的工作程序在传为张萱的《捣练图》中,却被打乱了。一幅手卷在手中徐徐展开,右边代表过去,左边代表未来,时间从右往左延展,捣练的故事缓缓讲出来——捣练(1)- 缝纫(3)- 熨烫(2)。如此一来,上述步骤略去第(4)个,第(2)第(3)出现反转。
这就是博士黄小峰发现的问题,传张萱《捣练图》呈现出来的制衣步骤,时间先后上显得并不十分连贯,该如何解释呢?由于目前留下来的可靠的唐代“捣练”图像(此处所指应为前述“线刻画”和“画像砖”)中没有熨烫的场景,黄小峰倾向于认为“熨帛”这个画题,在五代时才出现。在引述了对于周文矩和墓葬的考古发现之后,他推测“波士顿所藏的《捣练图》如果有祖本和原型,由于画面中出现了熨帛景象,其祖本年代便不可能是盛唐的张萱,而要晚到周文矩和阮惟德的时代了”。
黄小峰博士的论证非常精彩,旁征博引、逻辑清晰,笔者十分佩服。窃以为对于此图时间顺序上的不连贯似乎不排除还有其他解释。
暂且抛开卷轴这一形式不谈,这幅已经完全展开的画面仍然讲述着宫廷妇女聚集劳作的故事,先捣练再熨烫最后裁剪缝制,要使这个故事合理呈现,读图的顺序就应该是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最后在画面中间结束。

《捣练图》局部
这种画面构图方式在敦煌石窟本生故事画中常见,特别是睒子本生图(北周第301 窟),还有九色鹿本生(北魏第257 窟)。这两个故事与“捣练”故事相较都更为完整而复杂,发端由横向构图的两端开始,两条线索相向而行在画面中间迎来高潮(一个结局)。这是典型的“组合画式”,可视性比较强,在观看时视点会首先落在最富有感染力的地方,也正是画面中心所在。后来又发展出来的“连环画式”的变相,被认为相比之前的“单幅画式”变相的表现形式,可以使创作者更加从容地选择故事情节,然后将发生于不同时空中的情节在画面中有秩序地表现出来,叙事性特点十分明显,增强了对整个故事内容的表现。东南大学副教授于向东认为,古代印度、中亚等地的石窟变相中连环画式并不多见,单幅画式、组合画式则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而比较成熟的连环画式变相是佛教传入中土后的产物,在其产生过程中较多吸收了中土传统卷轴画和汉画像石的艺术经验。

敦煌壁画九色鹿本生局部
既然佛本生故事变相的描绘在构图上能够吸收卷轴画的经验,那么同样有理由认为画家在创作《捣练图》时可以借鉴“组合画式”从两端到中间的构思,如此便为黄小峰博士提出的问题给出了另外一种可以寻找解释的路径。笔者认为,画家打乱叙事顺序,主要因为构图上的考量,将相对静态的2人对坐理线缝纫场景置于画面中心,以三角构图稳压全卷气脉,两侧均为动势较大的站立劳作场景,右侧的圆形构图给人旋转、收缩的视觉效果,左侧的十字交叉形构图带来起伏、跳跃的心理感受。若将画面裁剪按连环画的叙事顺序重新拼贴,原本横向S 形的构图(一起一伏再一起),将变成两起一伏,似乐章戛然而止,对于注重对称均衡的古人来讲,无疑“动- 静- 动”比“动-动- 静”更加可取。